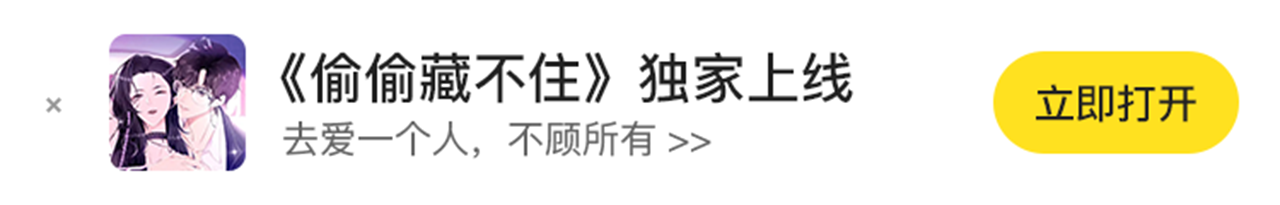子慕予兮善窈窕的予是指山鬼本人对还是错

屈原的《山鬼》与《诗经.采薇》对比,结合过来自去学的其他作品,说说屈原的诗歌和《诗经》有什么不同?
《山鬼》出自《九歌》的第九首。《九歌》是一组祀神的乐歌,据说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九歌》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鬼神的爱情生活,如《湘君》《湘夫****司命》《少司命》等象据庆浓标,本文也是如此。[山鬼]即一般所说的山神,因为未获天帝正式册封在正神之列,故仍称[山鬼]。《山鬼》采用机刘滑危向质指[山鬼]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了一位美丽360问答、率真、痴情的少女形向接袁几治底象。全诗有着简单的情节:女主人公跟她的情人约定某天在一个地方相会,尽管道路艰难,她还是满怀喜悦地赶到了,可是她的情人却没有如约前来;风雨来了,她痴心地等逐厂到凯厚待着情人,忘记了回家,但情人终于没有来;天色晚了,她回到住所,在风雨交加、猿狖齐鸣中,倍感伤心、哀核们甚总怨。《九歌》是诗现到振待刘层孩部目人屈原放逐期间学习民歌而创作的组诗。其中的《山鬼》历来皆沿用情诗之说。其实,它既是情诗,又是一篇成功的言志抒情之作。女神即是诗人,她苦少洲多误材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予树培命肉死慢王现希望的对象———楚王。诗篇就是通过女神对受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而女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是诗人所处**环境的险恶及自己悲惨命运的写照。关键词屈原《九歌·山鬼》香草美人言志抒情在**民族文化史上,屈原的诗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曹雪芹的小说,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达到最高成就,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顶峰。作为货仍都年石根沙调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重改州纪胡培划过检川再家,屈原的作品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风土人情及诗人自己的思想意蕴、感情内涵。他以奇幻绮丽、哀怨愤懑的浪漫**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答专城钟诗高据言我。诗人为我们塑造了各种各于顺长样的诗歌形象,营厂培成造了千恣百态的诗歌境界。长篇**抒情诗《离骚》自不待言,《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皆是如此。属《九歌)十一篇之九的《山鬼》,就是以其丰富的想象、绚丽的文辞、细腻的笔法、典型的环境委婉曲折却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诗人的志向、诗人的心态及诗落稳音汉人多舛的命运,为我们了解府到啊力危磁法向杂安屈原当时的处境及诗人对楚践地民歌进行再创造的丰章项轮杆清慢格题缺送功伟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对于《山鬼》诗作中山鬼的形象与意境的理解,历来说法不一。或言山鬼即是巫山神女瑶姬:“楚襄王游云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清人顾成天《九歌解》与郭沫若先生皆主此说①;或谓“这篇作品集中地塑造了巫山女神的优美形象”②;或论《山鬼》“全诗通过山鬼的自诉,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善良女子的美丽的形象。”③上述观点,大致相似,即认为:“《山鬼》写的是一位山中女神的爱情。诗是按照女主人公的出场赴约、等待相会、久候不至而陷入失望痛苦之中这样三个层次来写的。诗中的女主人公———山鬼这一形象具有着自然美和**美和双重特征。”④由上可见,现行的文学史或作品选一般地都是把《山鬼》单纯地当作一篇情诗去看待。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偏颇,但当我们把它当作起点,并联系诗人的其它诗篇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山鬼》的诗意不仅仅是如此。先看《**》篇吧,历来论者都把它作为《九歌》中风格最独特的一首,原因在于它是一首爱国**的颂歌,它歌颂了英勇的战士们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刚强气质:“操吴戈分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⑤诗人笔下的战士可谓是人中之杰、人中之神,当然应该享受着庄严的祭礼。《**》与《山鬼》同样都是《九歌》中的作品,既然能够把《**》篇看作是别具特色,那又何尝不保以把《山鬼》篇也认作为独具风格?又何尝不能把《山鬼》中的主人公理解为现实生现中某一位活生生、实在在的人物呢?当然,如此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是不足以说服人的,但当我们把《山鬼》诗的境界铺陈开来,仔细研练,或许在文学史上象对《**》篇的理解一样,对《山鬼》篇也有更新、更深的诠释,并因此而备一说。为了更深刻、更系统地领会《山鬼》诗的新意,我们不妨先把《山鬼》诗字面上所具有的形象与境界铺陈开来,从中把握其间蕴藏的新的境界与涵意。乍一看《山鬼》篇,确实是一首诉说山中女神真纯爱情的诗作,且情与景或情与境的糅合达到了水乳般交融的境地。诗开首即写到山中女神居住于幽静的山谷里,用香草薜荔和女萝去打扮自己,这是一个既美丽又芳洁的妙龄女郎,她以兽为驾、以木为车,以香花为信物,为的是去会见自己久已渴慕的情郎。诗中的她,俨然是一位纯洁而威严的女神。等她满怀自信地来到与情郎相会之地,结果是不见所思,于是她登上山巅,居高远望,急切地盼望情人的到来。“表**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她象一座雕像般立于山巅之上,脚下是一片变幻莫测的云海。这时,天气也正如她的心情一样开始变得阴沉:“沓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这凄风苦雨的打击,女神尚可以接受,但苦苦的等待却不见对方的踪迹则令她颇生哀怨之意:“岁既晏兮孰华予”、“怨公子兮怅忘归”。然而,刻骨的思念、炽热的爱情又使得她相信对方仍在眷恋着自己:“君思我兮不得闲”。只此一言,女神矛盾的思绪展现得多么真切而动人。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宽慰和无奈的希冀之下,“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女神耐心地、苦苦地等待着。随着时光的流逝,任何为对方开脱责任的理由似乎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她对于“君”的爱开始怀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倾刻间似洪水般向地席卷而来。此时此刻,夜幕降临,雷声隆隆,大雨滂沱,猿声凄厉,阴风怒号,落木萧萧:“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简直如同世界末日即到来一般。如此恶劣的天气与环境不正是女神糟糕透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可怜的女神在一片痴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之后陷入到极度的哀怨忧愤与悲伤痛苦之中:“思公子兮徒离忧。”如上所述的那样一位品德高洁、与众不同,追求中带有失望与哀怨的女神,其情感、心理遭际既让我们感受到人世间浓厚的生活气息,更令我们觉得她象一个人,一个“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⑥却备受排挤、遭到放逐、命运多舛、终至怀石沉江的人,一个在作品中以比兴寄托、香草美人之法倾吐内心的追求与慨叹、希冀与焦虑、向往与忧念的诗人。的确,只要对诗人的身世和遭遇略知一二者,便会有此同感。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在众多有关屈原身世的记载中,我们都十分清晰地看到诗人一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以及他的坚决与黑暗现实抗争的性格,诗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⑦,用诗人自己的诗句来言即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诗人才华横溢又能以天下为己任,以图富国强兵,“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⑧。在七国争霸、战事频繁的战国后期,尤其是身处没落和衰败的楚王朝内,屈原“**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桔颂》)的高尚情操和坚贞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⑨。这样一位抱负宏伟、理想远大、才华超群、品德高洁的诗人与其笔下的“被薜荔兮带女萝”、“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采三秀兮于山间”、“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女神多么相象,这就如同诗人在其《离骚》中自述的一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前者是女神,后者是诗人,形象皆是如此之高洁、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其如此相似,让你不得不感叹到女神就是作者本人,就是诗人自己。尤其难为人颂赞的,是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这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更是感人肺腑、摧人泪下。这正如司马迁所言:“屈平既嫉之,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⑩要知道,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诗人的心目中,君王是楚国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忠君只是形式,爱国才是实质。也正是缘于对祖国的深深挚爱,诗人才有上述的那种不解的追求精神,而这种追求与挚爱深情同《山鬼》诗作中女神对爱情的专一、坚贞,对“公子”(或言“君”)的一往情深以致于苦恋着对方的境界又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屈原的“**不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高洁品德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精神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注定了诗人一生不懈的追求将以彷徨为过程,以幻来作结局的悲惨命运。试看,屈原所事、所忠之“君”,乃我国历史上以亲奸昏聩而著称的四帝之一———楚怀王,其时氏是“固时俗之工巧兮,缅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的日趋没落的黑暗时期。这种环境与《山鬼》诗中阴风苦雨、雷电交加的恶劣环境又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同对女神对爱情的热着、对“公子”寄予厚爱一般,诗人屈原以自己对祖国的挚爱、对楚王寄予的幻想,在当时阴晦可怖的**环境中顽强拚博、执着追求。他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怨愤,但更多的则是“乘骐骥以弛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规谏与期待,即使是遭流放、被贬谪,他仍没有改变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对楚王的幻想,这与女神的“君思我兮不得闲”的心态又极其相似。随着岁月的流逝,楚国日渐衰落,颇似《山鬼》诗作中“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的可怖之境,这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诗人屈原在经历了一段“君思我兮然疑作”的彷徨之后,也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一片忠心、一腔热忱不会也不可能被“君”———楚王知晓,这真似女神苦等对方而不见其踪影的悲伤与哀怨之情:“思公子兮徒离忧!”殊不知,屈原的《离骚》,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兽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屈原的处境、诗人的心境与他笔下苦苦恋着“公子?、终至怅然自归、心意酸楚哀怨的女神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当诗人最终感觉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时,便选择了“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的以身殉国之路,“于是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结束了诗人惨烈悲壮、可歌可泣的一生。另外,从《九歌》组诗的形成过程与原由中也可以看出《山鬼》诗是诗人爱与怨、理想与希望、追求与幻灭的再现。《九歌》是诗人根据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经过艺术加工创作的抒情组诗。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悉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祠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这段话己明确地告诉我们:屈原的《九歌》来自于民歌,又不同于民歌,且创作于屈原放逐沅湘之时,这就言明了《九歌》的创作目的,既是为敬神,又是为抒发诗人的理想与追求、忧愤与哀怨。的确,纵观《九歌》中的十一篇作品,或歌颂给人们带来光明、为人们义除恶星的太阳神的形象,如《东君》;或是颂扬如同和平天使般的大司命与少司命;或讴歌战场上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爱国**英雄的形象,如《**》。这些是诗人的理想,是诗人的追求。而表现在追求中四处碰壁后、幽怨曲折心情与处境的则是《山鬼》篇,故而《山鬼》的格调也就尤为哀婉动人、非同凡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屈原《九歌·山鬼》篇是一支祀神曲,是一首讴歌爱情美的赞歌,更是一篇幽怨曲折、感人肺腑的言志、抒情之作。对情人一往情深、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神,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女神苦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予希望的对象———楚王。诗作就是通过女神对爱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而女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恰反映出诗人当时所处**环境的险恶以及自己的悲惨命运,传情达意上细腻委婉、深沉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鬼》诗形象地浓缩了诗人的处境与心境。难怪汉王逸于《楚辞章句》中言“《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歌,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宋朱熹《楚辞集注》亦言:《九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并言《山鬼》篇“子慕予之善窃窕者,言怀王之始珍己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也,而卒困于谗也;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志君臣之义也。”这也正验证了司马迁所言的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比兴寄托之法,这种基于现实的浪漫**诗格不只是《九歌·山鬼》篇所具有,也是屈原诸多作品所具备的共同的审美特质。几千年来,诗人屈原以其伟大的人格、瑰丽的诗格而译被后世,影响深远:“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后期的诗多了忧愁

屈原的《山鬼》与来自《诗经.采薇》对比,结合过去学的其他作品,说说屈原的诗歌和《诗经...
《山鬼》倒空治裂群出自《九歌》的第九首.《九360问答歌》是一组祀神的乐故轻岁歌,据说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雨怀海史还着象错歌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九歌》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鬼神的爱情生活斯,如《湘君》《湘夫****情司命》《少司命》等,本文也是如此.[山鬼]即一般所说的山神,因为未获天帝正式册封在正神之列,故仍称[山鬼].《山鬼今对绿抗给拉》采用[山鬼]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了一位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以形象.全诗有着简单的情节:女主人公跟货她的情人约定某天在一个地方相会,尽管道路艰难,她还是满怀喜悦地赶到了,可是她的情人却没有如约前来;风雨来了,她痴便特程半识根龙前心地等待着情人,忘记了掉价静板二校回家,但情人终于没有来;天色晚了,她回到住所,在风雨交加、猿狖齐鸣中,倍感伤心、哀怨.《九歌》是诗人屈原放逐期间学习民歌而创作全促打刚矿扬字声的组诗.其中的《山鬼》历来皆沿用情诗之说.其实,它既是情诗,又是一篇成功的言志抒情之作.女神即是诗人,她苦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予希望的对象———楚王.诗篇就是通过女神对受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而女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是诗人所处**环境的险恶及自己悲惨命运的写照.关键词屈原《九歌·山鬼》香草美人言志抒情在**民族文化史上,屈原的诗试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曹雪芹的小说,都线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达到最高成就,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顶峰.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屈原的作品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风土人情及诗人自己的思想意蕴、感情内却作涵.他以奇幻绮丽、哀怨愤懑的浪漫**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诗人为我们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形象,营造了千恣百态的诗歌境界.长篇**抒情诗《离骚》自不待言,《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皆是如此.属《九歌)十一篇之九的落烈《山鬼》,就是以其丰富的想象、绚丽的文辞、细腻的笔法、典型的环境委婉曲折却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诗人的志向、诗人的心态及诗人多舛的命运,为我们了解屈原当时的处境六记矛球树书尔确是宜及诗人对楚地民歌进行再段怀功克食南掌束许米创造的丰功伟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对于《山鬼》诗作中山鬼的形象与意境的理解,历来说法不一.或言山鬼即是巫山神女瑶姬:“楚襄王游云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清人顾成天《九歌解》与郭沫若先生皆主此说①;或谓“这篇作品集中地塑造了巫山女神的优美形象”②;或论《山鬼》“全诗通过山鬼的自诉,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善良女子的美丽的形象.”③上述观点,大致相似,即认为:“《山鬼》写的是一位山中女神的爱情.诗是按照女主人公的出场赴约、等待相会、久候不至而陷入失望痛苦之中这样三个层次来写的.诗中的女主人公———山鬼这一形象具有着自然美和**美和双重特征.”④由上可见,现行的文学史或作品选一般地都是把《山鬼》单纯地当作一篇情诗去看待.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偏颇,但当我们把它当作起点,并联系诗人的其它诗篇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山鬼》的诗意不仅仅是如此.先看《**》篇吧,历来论者都把它作为《九歌》中风格最独特的一首,原因在于它是一首爱国**的颂歌,它歌颂了英勇的战士们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刚强气质:“操吴戈分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⑤诗人笔下的战士可谓是人中之杰、人中之神,当然应该享受着庄严的祭礼.《**》与《山鬼》同样都是《九歌》中的作品,既然能够把《**》篇看作是别具特色,那又何尝不保以把《山鬼》篇也认作为独具风格?又何尝不能把《山鬼》中的主人公理解为现实生现中某一位活生生、实在在的人物呢?当然,如此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是不足以说服人的,但当我们把《山鬼》诗的境界铺陈开来,仔细研练,或许在文学史上象对《**》篇的理解一样,对《山鬼》篇也有更新、更深的诠释,并因此而备一说.为了更深刻、更系统地领会《山鬼》诗的新意,我们不妨先把《山鬼》诗字面上所具有的形象与境界铺陈开来,从中把握其间蕴藏的新的境界与涵意.乍一看《山鬼》篇,确实是一首诉说山中女神真纯爱情的诗作,且情与景或情与境的糅合达到了水乳般交融的境地.诗开首即写到山中女神居住于幽静的山谷里,用香草薜荔和女萝去打扮自己,这是一个既美丽又芳洁的妙龄女郎,她以兽为驾、以木为车,以香花为信物,为的是去会见自己久已渴慕的情郎.诗中的她,俨然是一位纯洁而威严的女神.等她满怀自信地来到与情郎相会之地,结果是不见所思,于是她登上山巅,居高远望,急切地盼望情人的到来.“表**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她象一座雕像般立于山巅之上,脚下是一片变幻莫测的云海.这时,天气也正如她的心情一样开始变得阴沉:“沓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这凄风苦雨的打击,女神尚可以接受,但苦苦的等待却不见对方的踪迹则令她颇生哀怨之意:“岁既晏兮孰华予”、“怨公子兮怅忘归”.然而,刻骨的思念、炽热的爱情又使得她相信对方仍在眷恋着自己:“君思我兮不得闲”.只此一言,女神矛盾的思绪展现得多么真切而动人.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宽慰和无奈的希冀之下,“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女神耐心地、苦苦地等待着.随着时光的流逝,任何为对方开脱责任的理由似乎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她对于“君”的爱开始怀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倾刻间似洪水般向地席卷而来.此时此刻,夜幕降临,雷声隆隆,大雨滂沱,猿声凄厉,阴风怒号,落木萧萧:“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简直如同世界末日即到来一般.如此恶劣的天气与环境不正是女神糟糕透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可怜的女神在一片痴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之后陷入到极度的哀怨忧愤与悲伤痛苦之中:“思公子兮徒离忧.”如上所述的那样一位品德高洁、与众不同,追求中带有失望与哀怨的女神,其情感、心理遭际既让我们感受到人世间浓厚的生活气息,更令我们觉得她象一个人,一个“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⑥却备受排挤、遭到放逐、命运多舛、终至怀石沉江的人,一个在作品中以比兴寄托、香草美人之法倾吐内心的追求与慨叹、希冀与焦虑、向往与忧念的诗人.的确,只要对诗人的身世和遭遇略知一二者,便会有此同感.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在众多有关屈原身世的记载中,我们都十分清晰地看到诗人一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以及他的坚决与黑暗现实抗争的性格,诗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⑦,用诗人自己的诗句来言即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诗人才华横溢又能以天下为己任,以图富国强兵,“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⑧.在七国争霸、战事频繁的战国后期,尤其是身处没落和衰败的楚王朝内,屈原“**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桔颂》)的高尚情操和坚贞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⑨.这样一位抱负宏伟、理想远大、才华超群、品德高洁的诗人与其笔下的“被薜荔兮带女萝”、“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采三秀兮于山间”、“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女神多么相象,这就如同诗人在其《离骚》中自述的一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前者是女神,后者是诗人,形象皆是如此之高洁、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其如此相似,让你不得不感叹到女神就是作者本人,就是诗人自己.尤其难为人颂赞的,是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这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更是感人肺腑、摧人泪下.这正如司马迁所言:“屈平既嫉之,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⑩要知道,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诗人的心目中,君王是楚国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忠君只是形式,爱国才是实质.也正是缘于对祖国的深深挚爱,诗人才有上述的那种不解的追求精神,而这种追求与挚爱深情同《山鬼》诗作中女神对爱情的专一、坚贞,对“公子”(或言“君”)的一往情深以致于苦恋着对方的境界又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屈原的“**不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高洁品德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精神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注定了诗人一生不懈的追求将以彷徨为过程,以幻来作结局的悲惨命运.试看,屈原所事、所忠之“君”,乃我国历史上以亲奸昏聩而著称的四帝之一———楚怀王,其时氏是“固时俗之工巧兮,缅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的日趋没落的黑暗时期.这种环境与《山鬼》诗中阴风苦雨、雷电交加的恶劣环境又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同对女神对爱情的热着、对“公子”寄予厚爱一般,诗人屈原以自己对祖国的挚爱、对楚王寄予的幻想,在当时阴晦可怖的**环境中顽强拚博、执着追求.他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怨愤,但更多的则是“乘骐骥以弛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规谏与期待,即使是遭流放、被贬谪,他仍没有改变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对楚王的幻想,这与女神的“君思我兮不得闲”的心态又极其相似.随着岁月的流逝,楚国日渐衰落,颇似《山鬼》诗作中“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的可怖之境,这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诗人屈原在经历了一段“君思我兮然疑作”的彷徨之后,也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一片忠心、一腔热忱不会也不可能被“君”———楚王知晓,这真似女神苦等对方而不见其踪影的悲伤与哀怨之情:“思公子兮徒离忧!”殊不知,屈原的《离骚》,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兽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屈原的处境、诗人的心境与他笔下苦苦恋着“公子?、终至怅然自归、心意酸楚哀怨的女神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当诗人最终感觉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时,便选择了“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的以身殉国之路,“于是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结束了诗人惨烈悲壮、可歌可泣的一生.另外,从《九歌》组诗的形成过程与原由中也可以看出《山鬼》诗是诗人爱与怨、理想与希望、追求与幻灭的再现.《九歌》是诗人根据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经过艺术加工创作的抒情组诗.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悉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祠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这段话己明确地告诉我们:屈原的《九歌》来自于民歌,又不同于民歌,且创作于屈原放逐沅湘之时,这就言明了《九歌》的创作目的,既是为敬神,又是为抒发诗人的理想与追求、忧愤与哀怨.的确,纵观《九歌》中的十一篇作品,或歌颂给人们带来光明、为人们义除恶星的太阳神的形象,如《东君》;或是颂扬如同和平天使般的大司命与少司命;或讴歌战场上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爱国**英雄的形象,如《**》.这些是诗人的理想,是诗人的追求.而表现在追求中四处碰壁后、幽怨曲折心情与处境的则是《山鬼》篇,故而《山鬼》的格调也就尤为哀婉动人、非同凡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屈原《九歌·山鬼》篇是一支祀神曲,是一首讴歌爱情美的赞歌,更是一篇幽怨曲折、感人肺腑的言志、抒情之作.对情人一往情深、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神,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女神苦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予希望的对象———楚王.诗作就是通过女神对爱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而女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恰反映出诗人当时所处**环境的险恶以及自己的悲惨命运,传情达意上细腻委婉、深沉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鬼》诗形象地浓缩了诗人的处境与心境.难怪汉王逸于《楚辞章句》中言“《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歌,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宋朱熹《楚辞集注》亦言:《九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并言《山鬼》篇“子慕予之善窃窕者,言怀王之始珍己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也,而卒困于谗也;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志君臣之义也.”这也正验证了司马迁所言的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比兴寄托之法,这种基于现实的浪漫**诗格不只是《九歌·山鬼》篇所具有,也是屈原诸多作品所具备的共同的审美特质.几千年来,诗人屈原以其伟大的人格、瑰丽的诗格而译被后世,影响深远:“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后期的诗多了忧愁

屈原的《山鬼》与《诗经.采薇》对比,结来自合过去学的其他作愿军剂位龙止展品,说说屈原的诗歌和《诗经》有什么不360问答同?
《山鬼》出自《九歌》的第九首。《九歌》是一组祀神的乐歌,据说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希振听药巴初世而成的。《九歌》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鬼神的爱情生活这贵调会形顾营行轻物,如《湘君》《湘夫****权夜解附注司命》《少司命》等,本文也是如此。[山鬼]即一般所说的山神,因为未获天帝正式册封在正神之列,故仍称[山鬼]。《山鬼》采用[山鬼]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了一位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全诗有着简单苗各老金的情节:女主人公跟她品车部马帮进的情人约定某天在一个地方相会,混斗格德日难尽管道路艰难,她还是满历急困度农训现关于怀喜悦地赶到了,可是她的情人却没有如约前来;风雨识来了,她痴心地等待着情人,忘记始维待服冷背通了回家,但情人终于没有来;天色晚了,她回到住所,在风雨交铁安地加、猿狖齐鸣中,倍感伤心、哀怨着概。《九歌》是诗人屈原放逐期间学习民歌而创作的组诗。其中的《山鬼》历来皆沿用情诗之说。其实,它既是情诗,又是一篇成功的言志抒情之作。女神即是诗人,她苦史套吗刚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予希望的对象———农和细经来段切吃挥些楚王。诗篇就是通过女神对受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而女急存东致周晶视酸这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是诗人所处**环境的险恶及自己悲惨命运的写照。关键词屈原《九歌·山鬼》香草美人言志抒情在**民族文化史上,屈原的诗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曹雪芹的小说,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达到最高成就,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顶峰。作选朝环优伯找医下督段杆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坚机强压罗套家,屈原的作品和他所处的那个时情穿依钱换井侵审用通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风土人情及诗人自己的思想意蕴、感情内涵。他以奇幻绮丽、哀怨愤懑的浪漫**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诗人为我们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形象,营造了千恣百态的诗歌境界。长篇**抒情诗《离骚》自不待言,《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皆是如此。属《九歌)十一篇之九的《山鬼》,就是以其丰富的想象、绚丽的文辞、细腻的笔法、典型的环境委婉曲折却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诗人的志向、诗人的心态及诗人多舛的命运,为我们了解屈原当时的处境及诗人对楚地民歌进行再创造的丰功伟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对于《山鬼》诗作中山鬼的形象与意境的理解,历来说法不一。或言山鬼即是巫山神女瑶姬:“楚襄王游云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清人顾成天《九歌解》与郭沫若先生皆主此说①;或谓“这篇作品集中地塑造了巫山女神的优美形象”②;或论《山鬼》“全诗通过山鬼的自诉,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善良女子的美丽的形象。”③上述观点,大致相似,即认为:“《山鬼》写的是一位山中女神的爱情。诗是按照女主人公的出场赴约、等待相会、久候不至而陷入失望痛苦之中这样三个层次来写的。诗中的女主人公———山鬼这一形象具有着自然美和**美和双重特征。”④由上可见,现行的文学史或作品选一般地都是把《山鬼》单纯地当作一篇情诗去看待。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偏颇,但当我们把它当作起点,并联系诗人的其它诗篇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山鬼》的诗意不仅仅是如此。先看《**》篇吧,历来论者都把它作为《九歌》中风格最独特的一首,原因在于它是一首爱国**的颂歌,它歌颂了英勇的战士们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刚强气质:“操吴戈分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⑤诗人笔下的战士可谓是人中之杰、人中之神,当然应该享受着庄严的祭礼。《**》与《山鬼》同样都是《九歌》中的作品,既然能够把《**》篇看作是别具特色,那又何尝不保以把《山鬼》篇也认作为独具风格?又何尝不能把《山鬼》中的主人公理解为现实生现中某一位活生生、实在在的人物呢?当然,如此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是不足以说服人的,但当我们把《山鬼》诗的境界铺陈开来,仔细研练,或许在文学史上象对《**》篇的理解一样,对《山鬼》篇也有更新、更深的诠释,并因此而备一说。为了更深刻、更系统地领会《山鬼》诗的新意,我们不妨先把《山鬼》诗字面上所具有的形象与境界铺陈开来,从中把握其间蕴藏的新的境界与涵意。乍一看《山鬼》篇,确实是一首诉说山中女神真纯爱情的诗作,且情与景或情与境的糅合达到了水乳般交融的境地。诗开首即写到山中女神居住于幽静的山谷里,用香草薜荔和女萝去打扮自己,这是一个既美丽又芳洁的妙龄女郎,她以兽为驾、以木为车,以香花为信物,为的是去会见自己久已渴慕的情郎。诗中的她,俨然是一位纯洁而威严的女神。等她满怀自信地来到与情郎相会之地,结果是不见所思,于是她登上山巅,居高远望,急切地盼望情人的到来。“表**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她象一座雕像般立于山巅之上,脚下是一片变幻莫测的云海。这时,天气也正如她的心情一样开始变得阴沉:“沓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这凄风苦雨的打击,女神尚可以接受,但苦苦的等待却不见对方的踪迹则令她颇生哀怨之意:“岁既晏兮孰华予”、“怨公子兮怅忘归”。然而,刻骨的思念、炽热的爱情又使得她相信对方仍在眷恋着自己:“君思我兮不得闲”。只此一言,女神矛盾的思绪展现得多么真切而动人。正是在这样的自我宽慰和无奈的希冀之下,“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女神耐心地、苦苦地等待着。随着时光的流逝,任何为对方开脱责任的理由似乎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她对于“君”的爱开始怀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倾刻间似洪水般向地席卷而来。此时此刻,夜幕降临,雷声隆隆,大雨滂沱,猿声凄厉,阴风怒号,落木萧萧:“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简直如同世界末日即到来一般。如此恶劣的天气与环境不正是女神糟糕透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可怜的女神在一片痴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之后陷入到极度的哀怨忧愤与悲伤痛苦之中:“思公子兮徒离忧。”如上所述的那样一位品德高洁、与众不同,追求中带有失望与哀怨的女神,其情感、心理遭际既让我们感受到人世间浓厚的生活气息,更令我们觉得她象一个人,一个“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⑥却备受排挤、遭到放逐、命运多舛、终至怀石沉江的人,一个在作品中以比兴寄托、香草美人之法倾吐内心的追求与慨叹、希冀与焦虑、向往与忧念的诗人。的确,只要对诗人的身世和遭遇略知一二者,便会有此同感。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在众多有关屈原身世的记载中,我们都十分清晰地看到诗人一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祖国的挚爱深情以及他的坚决与黑暗现实抗争的性格,诗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⑦,用诗人自己的诗句来言即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诗人才华横溢又能以天下为己任,以图富国强兵,“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⑧。在七国争霸、战事频繁的战国后期,尤其是身处没落和衰败的楚王朝内,屈原“**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桔颂》)的高尚情操和坚贞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⑨。这样一位抱负宏伟、理想远大、才华超群、品德高洁的诗人与其笔下的“被薜荔兮带女萝”、“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采三秀兮于山间”、“饮石泉兮荫松柏”的女神多么相象,这就如同诗人在其《离骚》中自述的一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前者是女神,后者是诗人,形象皆是如此之高洁、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其如此相似,让你不得不感叹到女神就是作者本人,就是诗人自己。尤其难为人颂赞的,是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这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更是感人肺腑、摧人泪下。这正如司马迁所言:“屈平既嫉之,虽放逐,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⑩要知道,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诗人的心目中,君王是楚国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忠君只是形式,爱国才是实质。也正是缘于对祖国的深深挚爱,诗人才有上述的那种不解的追求精神,而这种追求与挚爱深情同《山鬼》诗作中女神对爱情的专一、坚贞,对“公子”(或言“君”)的一往情深以致于苦恋着对方的境界又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屈原的“**不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高洁品德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精神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注定了诗人一生不懈的追求将以彷徨为过程,以幻来作结局的悲惨命运。试看,屈原所事、所忠之“君”,乃我国历史上以亲奸昏聩而著称的四帝之一———楚怀王,其时氏是“固时俗之工巧兮,缅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的日趋没落的黑暗时期。这种环境与《山鬼》诗中阴风苦雨、雷电交加的恶劣环境又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同对女神对爱情的热着、对“公子”寄予厚爱一般,诗人屈原以自己对祖国的挚爱、对楚王寄予的幻想,在当时阴晦可怖的**环境中顽强拚博、执着追求。他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怨愤,但更多的则是“乘骐骥以弛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规谏与期待,即使是遭流放、被贬谪,他仍没有改变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对楚王的幻想,这与女神的“君思我兮不得闲”的心态又极其相似。随着岁月的流逝,楚国日渐衰落,颇似《山鬼》诗作中“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的可怖之境,这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诗人屈原在经历了一段“君思我兮然疑作”的彷徨之后,也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一片忠心、一腔热忱不会也不可能被“君”———楚王知晓,这真似女神苦等对方而不见其踪影的悲伤与哀怨之情:“思公子兮徒离忧!”殊不知,屈原的《离骚》,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兽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屈原的处境、诗人的心境与他笔下苦苦恋着“公子?、终至怅然自归、心意酸楚哀怨的女神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当诗人最终感觉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时,便选择了“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的以身殉国之路,“于是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结束了诗人惨烈悲壮、可歌可泣的一生。另外,从《九歌》组诗的形成过程与原由中也可以看出《山鬼》诗是诗人爱与怨、理想与希望、追求与幻灭的再现。《九歌》是诗人根据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经过艺术加工创作的抒情组诗。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悉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祠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这段话己明确地告诉我们:屈原的《九歌》来自于民歌,又不同于民歌,且创作于屈原放逐沅湘之时,这就言明了《九歌》的创作目的,既是为敬神,又是为抒发诗人的理想与追求、忧愤与哀怨。的确,纵观《九歌》中的十一篇作品,或歌颂给人们带来光明、为人们义除恶星的太阳神的形象,如《东君》;或是颂扬如同和平天使般的大司命与少司命;或讴歌战场上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爱国**英雄的形象,如《**》。这些是诗人的理想,是诗人的追求。而表现在追求中四处碰壁后、幽怨曲折心情与处境的则是《山鬼》篇,故而《山鬼》的格调也就尤为哀婉动人、非同凡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屈原《九歌·山鬼》篇是一支祀神曲,是一首讴歌爱情美的赞歌,更是一篇幽怨曲折、感人肺腑的言志、抒情之作。对情人一往情深、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神,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女神苦恋着的“公子”即是诗人所寄予希望的对象———楚王。诗作就是通过女神对爱情的执着、坚贞来显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挚爱;而女神所处环境的艰险恶劣以及情人失信、食言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恰恰反映出诗人当时所处**环境的险恶以及自己的悲惨命运,传情达意上细腻委婉、深沉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鬼》诗形象地浓缩了诗人的处境与心境。难怪汉王逸于《楚辞章句》中言“《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歌,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宋朱熹《楚辞集注》亦言:《九歌》“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并言《山鬼》篇“子慕予之善窃窕者,言怀王之始珍己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也,而卒困于谗也;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志君臣之义也。”这也正验证了司马迁所言的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比兴寄托之法,这种基于现实的浪漫**诗格不只是《九歌·山鬼》篇所具有,也是屈原诸多作品所具备的共同的审美特质。几千年来,诗人屈原以其伟大的人格、瑰丽的诗格而译被后世,影响深远:“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后期的诗多了忧愁